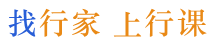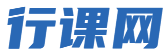例如,華為不僅在5G技術領域全球領先,集聚了19萬名優秀的員工,而且確立了“聯接”戰略,幫助人們實現“聯接”,進入數字世界與智能社會。
騰訊不僅在社交技術應用領域提升了超過10億人的生活水平,還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連接器”,賦能產業伙伴,實現數字化轉型。
這一切,都引發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重新發現與認識企業的價值。那么,協同共生論應運而生,它最早由陳春花教授在《協同共生論》書中提出。
協同共生是指共生單元通過不斷主動尋求協同增效實現邊界內組織成長、跨邊界組織成長、系統自進化,進而達到整體價值最優的動態過程。
協同共生可分組織內部、組織外部和跨組織三種情況。
內部協同共生是指企業生產、營銷、技術、供應以及管理等環節各自創造價值卻又協同作戰產生整體效應。
外部協同共生是指價值網絡中的企業由于相互協作,共享資源和能力,獲得比作為一個單獨運作的企業更大的成長空間。
跨組織協同共生是指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中的企業通過相互協作共創,創造出原行業或原領域從未有過的新價值。
協同共生效應的本質就是通過構建共生體系獲得協同增效。其實,關于協同共生可以追溯到6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
1.
早在1969年,德國科學家赫爾曼·哈肯提出“協同論”這一概念,他對協同的界定是:“系統的各部分之間相互協作,使整個系統形成微觀個體層次所不存在的新的結構和特征。”哈肯的協同論認為:世界萬物都普遍存在有序、無序現象;在特定情境下,有序與無序能互相轉化;無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協同。
顯然,在工業時代,人們習慣于關注競爭以及如何獲得競爭優勢的研究。即通過競爭尋求競爭優勢的確給企業帶來了價值,但是,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行業邊界的融合以及創新價值的不斷涌現,疫情之后的協同工作模式,以及企業間、組織間的合作共生,越來越凸顯協同共生價值的優勢。即從關注競爭,轉向關注協同,也從理解自身發展,轉向必須理解自身與外部的共生發展。
關于這一點,在更早一些,美國戰略理論專家伊戈爾·安索夫于1965年在管理學界首次提出“協同”的概念,并運用投資收益率(ROI)確定了協同的經濟學內涵,他指出,各業務單元間的有機協作能使企業整體價值大于各部分價值的簡單加總,產生“2+2=5”的協同效應。
安索夫提出了一個協同定義公式。該公式說明,一家產品系列齊全的企業與只生產個別產品的企業相比,可以在單一產品上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率,即企業整體價值大于企業各獨立組成部分價值的簡單加總。同時,安索夫指出:“大多數企業由于存在規模優勢,即一家擁有完整產品線的大型企業的總銷售量與許多小企業總共的銷售量一樣,但它的經營成本卻不高于各小企業經營成本的總和……在投資既定的情況下,一家擁有完整產品線的企業比起參與競爭的多個獨立的企業,通常可以體現更高的營業收入和/或更低的經營成本的優勢。”由此可見,如果一家公司能通過產品與市場組合來產生協同效應,那么該公司就可以在市場中獲得優勢。
產品P1的年收益率ROI可以表示為:ROI=(S-O)/I
S——一種產品帶來的年銷售收入;
O——產品運營成本;
I——戰略投資,即為了開發產品、購置設備和設施以及建立銷售網絡,必須在產品開發、市場開拓、設備、建筑、機械、存貨、培訓及組織發展方面進行的投資。
對于產品線上所有的產品P1,P2,…,Pn,也會有相應的表達式。如果產品間不存在任何相關性,則企業的總銷售額為:ST=S1+S2+…+Sn。
同樣,運營成本和戰略投資為:OT=O1+O2+…+On,IT=I1+I2+…+In。
如果各產品銷售收入、運營成本和投資成本互不相關(約束條件),公司的總體收益率則低得多。但大多數企業存在規模優勢,即一家擁有完整產品線的大型企業的總銷售量與許多小企業總的銷售量一樣,但它的經營成本卻不高于各小企業經營成本的總和。
關于安索夫提出的協同公式,可以從平衡計分卡的創始人羅伯特·卡普蘭和戴維·諾頓的組織協同得到充分論證。組織協同是一項關鍵管理流程,它將企業、業務單元、支持單元、外部合作伙伴、董事會與公司戰略銜接起來。卡普蘭和諾頓認為組織協同的來源分別是財務協同、客戶協同、內部流程協同、學習和成長協同,并將這一評價體系命名為“平衡計分卡”。
平衡計分卡是一個協同企業戰略和組織架構的系統,管理者在應用平衡計分卡時需要先描述企業戰略,然后再探討如何運用戰略地圖和平衡計分卡實現組織架構與戰略的協同。管理者在實踐中感受到,除非企業利用衡量和管理系統將它們的組織架構與戰略協同起來,否則很難找到最佳的工作機制。有效的平衡計分卡通過構建重要指標體系之間的一致性與關聯性,讓員工通過協同促進戰略實現。
卡普蘭和諾頓認為,組織協同的責任在總部,并闡述了企業高管層如何通過構建集團層面的戰略地圖和平衡計分卡,來形象地描述集團的“價值定位”——如何在不同的業務單元之間創造協同效應,如何運用平衡計分卡管理體系協調和管理高層戰略實施。
為了讓管理者能夠更好地理解戰略與組織流程之間的協同關系,卡普蘭和諾頓指出,組織協同流程要循環且“自上而下”,理想的組織協同應該由總部定義,下屬單元執行。通過在業務部門、職能部門與外部合作伙伴之間產生協同效應,企業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在內部流程協同方面,設計了多個協同查驗點,通過對企業價值創造的典型流程和步驟的分析、查驗,力圖在呈現企業總部價值定位的基礎上,明確把握影響企業在業務部門、職能部門、外部合作伙伴之間產生協同效應的關鍵環節。
2.
哈肯、安索夫、卡普蘭與諾頓的研究,幫助人們理解了動態變化中協同的效應及作用,這些探討雖然也涉及對組織外部的思考,但主要是在組織內部的各要素之間展開的。在今天組織所依存的真實環境中,我們還需要基于組織與外部的關系來探討協同效應的問題。從這個視角出發,康德的關系范疇、貝塔朗菲的整體論與馬古利斯的共生理論給了人們有意義的幫助。
康德認為,萬事萬物只有在協同性中才能現實存在,凡是需要認識的都要和其他事物發生作用。按照康德范疇表中關于關系范疇的描述,協同是主動與受動之間的交互作用。
貝塔朗菲的系統哲學,指出需要用整體的、系統的視角重新審視研究對象,并強調系統的整體性、層次性、關聯性和一致性,這是對傳統的、機械的還原論的直接否定。
貝塔朗菲的整體論是把對整體的思考放在對局部的思考之前,不會因為想要了解企業而對其進行“分解”,在支離破碎的殘骸識別中進行判斷。現實問題極少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與其他問題相伴而來的。處理單個問題會涉及多個利益相關者,牽一發而動全身,一旦處理不當,便會陷入“亂題”之中不可自拔。
德魯克曾經明確指出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整體,一個大于各個組成部分總和的整體,一個富有效率的整體,投入其中的各項資源所帶來的產出一定要大于投入資源的總和”。任何沒有整體觀念的管理方案,在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都會導致整體利益的損害。
值得一提,與達爾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不同,美國生物學家林恩·馬古利斯認為,達爾文關于進化由“競爭驅動”的想法是不完善的,共生才是漫長進化時代的“閃光點”。
馬古利斯認為,共生是一種普遍的生物學現象,是在人類出現前很長時期內就存在的。在她看來,共生不等于互利共生。“共生是無處不在的”“共生是進化創新的源泉”“共生是在生物新穎性產生上的一次革命”。
如《海底總動員》里的主角小丑魚和海葵就屬于共生關系,海葵擁有帶刺的觸角,可以保護小丑魚及它們孵化的胚胎免受外來物種的攻擊;小丑魚在和海葵接觸后分泌的黏液,可以為海葵對付以海葵為食的魚類建造防御工事,因此小丑魚和海葵之間共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用馬古利斯的觀點“生命并不是通過戰斗,而是通過協作占據整個全球的”話來說,共生是自然進化的機理,通過共生,世界才可以保持事物的多樣性;通過多樣性的個體之間復雜多維的交互協同作用,不斷創生新物種,世界才得以不斷發展與進化。
3.
對這些經典理論的理解,再與數字化時代環境的基本特征融合在一起,便構建了新的組織管理方法——協同共生論。它告訴我們以整體論的視角去看待今天的世界,以共生去理解生命自然進化——只有基于多樣性、交互作用,才可以產生新的價值。
正如哈肯所言,“取更長的時間鏡頭,合作是秩序形成過程中的主流現象。沒有部件之間的合作,所有的有機體都將無法存活;沒有有機體之間的合作,生態和社會系統將不復存在。從混沌到秩序,合作具有必然性。”
無疑,數字化為“協同共生”提供了成長與發展的“營養液”。數字化所形成的連接,實現了不同場景要素、跨產業邊界等多樣化觸點的自由組合,實現了新的價值創造。